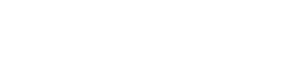对如今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活了二十年的温化平来说,对老师、广院、祖国这三个词的感觉仿佛扭成了同一股强烈的情绪,一股饱含着思念的情绪,在每每回首往日的时候都会席卷而来。当年,任远老师不顾学校的批评指责,做主录取了她这个唯一没有经过面试的学生。任远老师说,“人家高考成绩那么好,又在公安局工作,政治和业务都这么优秀,不就是没见面嘛?”这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举动为温化平换来了四年的精彩时光。2010年任远老师去世,温化平心中有说不出的伤心难过,不过可以告慰的是,她这个当年的“唯一”从入校开始直到往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从未停止过努力和追求,没有让任老师失望。
温化平:2002年,在毕业20年聚会时,我见到了当年的系主任矫广礼老师。矫老师见面一句话:“你过得好吗?我真是挺惦记你的!跑得那么远。”问得我泪如雨下,是啊,真是跑得太远了。
思念具备一种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特异功能,于是有些人、有些事,即使远离到只剩下了模糊的轮廓,却依旧可以长长久久地留存于一个人的心绪中。对这31个蓄势待发的长跑者来说,广院是人生的起跑线,老师则是给予参与资格然后帮助他们调整起跑姿势、告知注意事项最后大喊一声加油的人。当他们跑远之后,老师的身影越来越小,甚至也很少有人再回头看,但起跑线上发生的一切对于长途跋涉的人来说,都是再也回不去却永远最重要的开始。
09.从物质到精神
比起视觉和听觉,有时嗅觉和味觉更能把人拉回到一段早已尘封的记忆中去。尤其是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美食越是稀少,饱餐后的满足感就越是强烈,特定岁月的美好气味也就越是烙得深刻。在很多人心中,相比如今眼花缭乱精致绝伦的佳肴,那时凭票限量的食物哪怕品相笨拙、味道打折,也能够不战自胜。
毕竟,因想念而得胜的不仅是食物,更是那个回不去的时代,还有那个时代里即使缺食少穿,即使没有选择,却仍旧蓬勃向上、意气风发的自己。
广院食堂,谁主沉浮?
上世纪80年代的广院食堂是个又冷又空旷的大礼堂,只有几十张方桌子,却没有椅子,全校学生吃饭都得站着。最让学生们印象深刻的几道菜里,熘肉片算是一道,听起来很过瘾,实际上就是白菜梆子炒少许肉片而已;还有小黑板上写着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红豆腐”,5分钱,其实就是不想刺激人所以改了名的猪血;还有苜蓿肉、拆骨肉以及一份六个的小丸子、一份两个的狮子头;另外就是丝糕——放了糖精的玉米面蒸出来之后的一大盘发糕。早餐是北京丝、臭豆腐还有玉米粥;到了西瓜下来的季节,温化平还会很大方地给男生们买一个大西瓜。
黄著诚:四年下来,我这样土生土长的“南蛮”也渐渐习惯了窝窝头、北京丝儿,甚至还爱上了臭豆腐,不知不觉就培养出了北方人的口味。现在的我,即使住在五星级顶级酒店,面对各种烘焙得香气喷鼻的面包、黄油也不怎么动心,但是只要遇到这些珍藏在记忆中的食品,依然会经不住诱惑偷尝几口。
柳春江和乔保平都做过生活委员,他们每月去校办领回每人总共36斤的面票米票粗粮票,然后把这些薄薄的纸片裁好分给大家。米票有7斤,最受南方同学欢迎;面票能买馒头面条;而粗粮票只能买到玉米面、红薯、高粱面这最不招人待见的“三面”。那时班里盛行着一个互惠互利的好办法,那就是爱吃米的南方同学和爱吃面食的北方同学交换饭票,各取所需。除此之外,很多胃口较小的南方同学还可以把剩余的面票拿到相邻的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换鸡蛋,换花生米,补补身体。
在广院,有两件事最最受大家重视:一是学习,二是吃饭。对于拼命啃书外加玩命打球的男孩儿们来说,一日三餐绝对是动力之源。当时广院的伙食并不好,同学们对常常大幅动作抖勺导致菜量可怜的厨师颇有意见却敢怒不敢言。每次学院开会,各年级各班反映最多的就是食堂差、伙食差,又贵又少。
作为院学生会主席的岑传理代表学生会多次和后勤部门交涉,不过成果并不明显。于是有一天他决定豁出去解决一下这个工作难点,于是带人闯进了院长办公室。
岑传理:院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显得很民主。问我们有什么管理办法和好的建议,我提出可以试试以兵管兵,让学生各班轮流下食堂帮厨,同时让各窗口由学生卖饭,统一结算。此招学校领导说可以和食堂商量。我想,各院校无此先例,让大学生卖饭,天下奇闻,也没抱太大希望。
一周之后,学生会接到学校通知,食堂新管理办法出炉:每班轮流帮厨并卖饭一周。从此,在卖饭窗口里,学生们亲切的面孔换掉了大师傅的“冷脸”。遇到自己班同学买饭时,卖饭者的菜勺还要再少抖两下,于是饭菜大大丰盛过从前。第一个月月底结算时,食堂收入超过了以往,于是超出的部分全部补到下月伙食费中。很快,广院食堂还出现了“佛跳墙”——又便宜又实惠、肉多菜香的伙食引来各大院校师生观摩取经,二外的学生更是经常闻味“跳墙”而来。
77摄影班里有个“卖饭代表”,也绝对称得上是学校的帮厨模范,他就是刘建新。
程鹤麟:忘了从哪天开始,不知他如何打入学校食堂内部,反正突然有一天大家惊喜地发现,学生食堂的售卖窗口里,巍然屹立着我们77摄影班的刘建新。他笑容可掬态度殷勤动作麻利,收饭菜票,唱饭菜名儿:鱼香肉丝一份,米饭半斤,馒头五个……在用餐高峰时段为忙碌的厨房义务帮工,他是厨房工友眼里的活雷锋;为77摄影班同学敞开了优先买饭买菜的后门,他是全班同学的贴心人。
永远笑眯眯、一脸富态的刘建新,很像专职大师傅,有不少79级新生都把他当成了“真厨师”。他仿佛特别了解同学们心中的“真正需要”,于是每次都早早到达食堂,带着一帮人“占领”打饭窗口。
刘建新:大三和大四,我都一直在食堂里头帮厨。因为当时在学校里头,没有更多的社会服务的机会和岗位,作为我来说,真是想为大家做点事。当时食堂确确实实人手很紧张,所以我就跟食堂的大师傅们联系了一下,他们当然非常高兴。其实我也就是帮着打打菜,那时候吧,如果看到我们自己班上同学,那这个菜肯定就要多半份,这种关心实际上是特别朴素的。我现在虽然是河南台管新闻的,但也有点不务正业,也管管食堂。没有别的,也还就是想为大家服务。学校对我的培养和我现在的工作每一个地方都是有联系的。
刘建新的细心和对同窗好友们的热心在韩国强的印象中也十分深刻。
韩国强:记得每次我们下馆子,他都要先拿醋壶倒一碗醋,然后把大家所有的筷子、勺子都涮一涮再让大家吃。他自己会带一个勺子,有鱼什么的,都要帮大家分好。他想得特别周到,包括现在把他们河南电视台的后勤也抓得不错,食堂很出名。
大食代
当时的北京,是很多外地人向往的地方,城市面貌和物质供应都要比各地高出一大截。拿黑龙江来说,粮食供应还是25%的细粮、75%的粗粮,但如果到了北京,用全国粮票来换北京粮票的话,米面占到75%,粗粮只占25%。除了蔬菜品种丰富,供应充足外,北京的肉类供应也非常令人羡慕。北京市民买一斤肉需要交一斤肉票,但如果买两毛钱的肉,则不需要交肉票。两毛钱的肉也有薄薄的一条,足可以炒一个菜了。于是在广院上学对于外地到来的学生们来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时大学生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是12元钱。两毛五能吃一顿挺好的饭,最贵的菜两毛钱,叫做烧茄子,有一点肉,茄子是油过的。剩下的还有5分钱,甚至两分钱的菜。一天平均花上个四五毛钱,那么12块钱就可以撑着吃一个月,后来慢慢涨了点,大概涨到20块钱。在吃饭的问题上,带工资入学的同学就“豪气”了不少。比如一个月拿40多块钱的钟大年,他很豪爽,所在的小组不论是外出活动还是下馆子改善生活都常常花他的钱。不过比较起来,小组成员王桂华还是最最获益者,因为钟大年一直到现在还在单请她。
程鹤麟:钟大年这项个人优良传统已经保持了三十多年了:热爱买单——凡同事同学聚餐,除非哪个傻小子提前声明(有时提前声明也没用),否则最后买单的一定是钟大年老师或同学。
钟大年:那时候,我们小组六七个人去王府井东来顺吃一顿涮羊肉只要10块钱,不过那也已经是我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了。唉,记不清有多少次小组活动,也不知道花了我多少钱,只知道毕业后第二周我结婚的时候,存折里只有100多块钱了。好在太太没有埋怨我,因为,她就是我们小组受益的成员之一。
细数班里胃口最好最贪嘴的主儿,一定不能漏掉了周五一和王小幸。这两个人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宣布肉涨价的头一天,急急赶往东四的一家湘菜馆,虽然并不丰盛但却心满意足地享受了最后一次低价晚餐。廉价的时代早已不复返,之后的三十多年若干次的涨价事件引发过无数次抢购潮,抢米,抢盐,抢油,甚至抢手纸,不过这两个人凭着“抢吃”行动成了中国“抢购”历史中的先驱。
在77摄影班,田广和黄著诚拿的是最高助学金,外加3元的少数民族补助,两人关系挺亲密。不过田广总是独自在另一个食堂吃饭,这让黄著诚很不理解,认为他多此一举。
黄著诚:有一次没忍住终于问了他一句,为何不吃猪肉,不都是蛋白质吗?田广反问我:“你吃毒蛇吗?吃老鼠吗?”我说:“吃啊!”(我们在家乡从小视蛇鼠为美味)。田广大怒:“吃蟑螂吃苍蝇吗?那也有蛋白质啊!”那时的我没见过太多世面,也是第一次接触穆斯林,真不知道还有不吃猪肉的民族。过了许多年,一提起这件事,我和田广还是觉得饶有趣味。
每年寒暑假结束后回校,很多外地同学都会带来家乡的特产供宿舍好友们品尝,比如乔保平会带兰州又大又扁的黑瓜子,徐佳伦会带杭州的山核桃,现在看来最牛的是李讯,他带的特产是茅台酒——1978、1979年的茅台酒。
李讯是贵州人,当过兵,为人颇为严谨,在和同学交往的过程中一般不主动说话,也不太发表意见,但是他每一年回家的时候,都要从家里带瓶茅台酒过来。不过室友们都没怎么喝过酒,不习惯,觉得非常辣口,刚开始还象征性地尝一尝,后来连尝都没人尝了——全中国最好的酒就这样被无情冷落。不过世上总是存在着有口福的聪明人,那就是马国力,大半瓶茅台酒最终都会落进他的肚里。不知现在想起来,马先生会不会偷着乐。
入党!入党!
77摄影班入学的时候,已经有13位同学是中共正式党员、1名预备党员。班长任金州,党支部书记岑传理,副班长钟大年等人成了积极推进班上其他“群众”入党事宜的决策团。
胡立德:我们班党支部书记岑传理、班长任金州、副班长钟大年,像三位老大哥,很关照我们这帮弟兄。尤其是班长,不仅像老大哥,还特别爱操心,很能张罗事。有他们在前面带头,大家很容易就聚在一起了。
当时的班长任金州脑子里有个强烈的意识,那就是在大学入党一定比单位入党容易得多,所以一定要尽可能多地解决同学们的入党问题,一定要多发展党员。一旦成为党员之后,就立刻拥有了更大的竞争力,将来就业之后就能够比别人快走一步。1981年3月17日晚,77摄影班党支部召开了第一次新党员发展大会,讨论并投票表决徐佳伦、胡立德的入党申请,全班13名正式党员和1名预备党员全体参加了会议,申请入党的其他同学韩国强、刘建新、刘新荣、孙林、高燕文、王小幸、王政、段晓明、余义宁、田广、鲁伟、黄著诚等也列席了会议。经过讨论和投票表决,徐佳伦、胡立德获全票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预备党员。
徐佳伦当场表态说:“感谢同学们对自己的帮助,这是对我的鞭策,虽然大会通过了,还有待于上级党委批准,预备期还有一年,今后我还要更加努力接受组织的考验,要在思想上入党,真正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胡立德也表态说,“参加支部大会很受教育。大家提的意见一是真诚,二是准确。大会接受我为预备党员,上级无论批准与否,都是对我的鼓励与考验,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同宿舍同学乔保平、钟大年是徐佳伦的入党介绍人,乔保平在徐佳伦的入党申请登记表中写下了这样的介绍人意见,“徐佳伦同志对党的认识明确,政治思想进步;有较强的自觉精神和严格作风;学习努力,德智体全面发展,工作责任心强;纪律性和组织观念强;能普遍联系和团结群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该同志在工作中偶有急燥现象,本人同意并介绍徐佳伦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3月16日”。
在班党支部和班委的努力下,77摄在大学期间发展了四位党员:徐佳伦、胡立德、韩国强、刘建新。
任金州:韩国强在学校里是成长型的人,从业务上讲没有刘惠东那么聪明,也没有马国力那种文才,更没有孙林外语的优势,他在各个方面不是最突出的。但韩国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坚毅、执著,山东人的那种执著。他心里有想法,在做所有事时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一直不断地激励自己往前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在全班积极踊跃争取加入党组织的火热圈子外边,站着两个“超然脱俗”的人,那就是从未写过入党申请书的俞建成和刘惠东。他们看似与入党事宜毫无关联,但事实上,这两个人是“躲在暗处”的关键两票。
俞建成:我们班里只有我和刘惠东没写入党申请书,我们不积极靠拢组织,所以政治地位属于最底层,但同时也变身为最稀缺的资源。每当我们宿舍的党支部书记岑传理同学要征求群众意见的时候,说的就是征求我俩的意见。我们是群众嘛,群众关系好不好,就是跟我们两个的关系好不好。我们的两票很重要哦,所以在学校入了党的同学,你们一定获得了我俩的两票。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