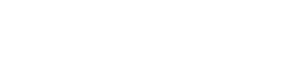王桂华:北京广播学院在定福庄,北京电影学院在朱辛庄,这两所地处偏僻郊区的学院,一所是培养电视人,一所是培养电影人,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说在少有的摄影展、画展上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就是常客,因此我和电影学院78摄影班的女生在摄影展相识,至今都是好友。
为了看一次画展或影展,有同学拿着借来的月票或是自己画的月票进城。月票一般是男生跟男生借,女生跟女生借。但是,更夸张的是,竟然有大胆的男生,拿着女生的月票也敢蒙混过关。
同过班和同过小组的不一样,同过小组的和同过宿舍的又大不一样,在一起“睡过的”印象就格外深刻。且让我们共赏鲁伟同学的妙笔生花——《在同一宿舍睡过的那些人》。
——黄著诚,来自壮乡广西,我们亲切地叫他“阿黄”,可能是套用“刘三姐”中的“阿牛”来的吧。压根儿就没想做官的他,参加工作后却一直在做官,他荣获“韬奋奖”的时候,我还在干着“淘粪”似的蓝领苦累活儿。在校期间,阿黄睡在我的上铺,他熟睡后的样子很特别,眼睛始终是微睁的,想对他下手干点什么坏事儿得掂量一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看得见呢。阿黄还有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他看书时的姿态,可以用“端坐”来形容,腰板儿很直,眼睛和书的距离保持着教科书式的规范,且神情极为专注。最雷人的事,算是他最初与大家一起在公共大澡堂洗澡……算了,此处省去25个字,还是给现在做局领导的黄局长留点隐私吧。
——马国力,宿舍里唯一的一个北京人,带工资上学,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外地愣小伙儿,与他始终有一种距离感。当时,在我眼里他既是个大哥也是个“大款”,可夏天穿着后背尽是窟窿的“和尚领儿”,没个款样儿。他刚开始还总主动让我和田广抽他的不带过滤嘴儿的“香山牌”。打那儿以后,不管他主动还是不主动,反正我是再也没买过烟抽,“香山牌”始终放在他的床头,从未断过档。临毕业之前,老马不无欣赏看着我说,小伙子这几年被熏陶的啊……说半截话是老马的习惯,下半句我想可能是“有个人样了”吧,在老马眼里,我在没“熏”之前,还指不定是啥样子呢。
——柳春江,一个脑容量很大的江西“老表”,一个性情宽厚的兄长。据说他的一篇题目叫做“九月九”的高考作文还被选为77年的高考范文。“聪明绝顶”的他,在校期间的发型就已经酷似毛主席,心想真的不愧为革命老区的革命后代,连发型都要追随革命领袖。老柳是个电影篓子,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电影没他没看过的,说起电影那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人啊,有长项就有短板。智力超群的老柳体能一般,胳膊柔软得像个女人,遇到体育课玩单、双杠,老柳绵软的双臂艰难地支撑着大头的样子,甚是让人同情。
——刘新荣,一个新疆来的汉族小伙儿,一个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纯爷们。这个纯爷们天生不怎么长胡子,说话声音小却节奏快,走路步幅小但步频快。他在平常拿物件时,不经意间小手指就很自然地翘起来,这时总会让我抓个现行。私下里,我就叫他“荣荣”。荣荣性情温和,心地极为善良,与世无争,观察力很强,记忆力很好。荣荣经常揪住我说,你看你看,怎么能这样!久而久之我发现荣荣还是有“脾气”的,这个“脾气”源于他对事物的一贯看法,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很坚守。在校期间我们关系很好,记得我打篮球时被打断了门牙,只有他三番五次陪我往返于学校和北医大附属口腔医院。
——田广,一个来自宁夏的回族小伙儿。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一年四季都堆在床铺上的那件老羊皮袄,实际上那是一件军大衣,是长城以北的解放军冬装的标准装备。在那个年代,那是件不是谁都能搞得到的奢侈品。田广很安静,囿于自己的世界里,不大与人交流。
——王屏,一个来自河南的江苏人。此仁兄除了鼻梁有一点点不易察觉地偏左以外,可以算是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与我这样不到20岁,还有些天真稚气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老练得多。在宿舍里虽然我和他床铺相对,但却有咫尺天涯之感。
若把77摄影班比喻成一个江湖,来自浙江的俞建成和湖南的刘惠东显然不属于少林武当大派系,而是独门小道上的少数派。在一个“文革”余温尚在的年代,他们来去自由,保持独立的个性做派显然是奇葩两朵。
俞建成:无独有偶,学校上学的四年,居然还有一个刘惠东和我相似,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们的行为却如出一辙。记得夏天军训时,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趴在烈日暴晒的野地里练射击,唯独我俩在宿舍的房间里悠哉悠哉休闲着。我俩都是学校乐队的,在晚上九十点钟,同学们都想静下来看书,而我俩把铜管吹得无比嘹亮,气得住在楼上编采班的学友们直摔脸盆,可也没人前来当面说我们,而住在我们隔壁宿舍的我们班的同学,当然更不会有话了。
从上小学开始,俞建成同学就是一个要求上进的学生,在班里一直当班长,直至高中毕业。到了农村,又是知识青年的小组长。到了工厂,第一年就评上整个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但是进了大学,他似乎改头换面,当了一回后进。若干年后,俞同学将自己的后进总结为体制范畴内的后进,在道德范畴,他一直是一个先进的人。体制范畴中的后进,却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如此地自由自在,这是俞同学万万没想到的。现在想来,在体制内后进的人,属于靠墙站着的,无路可退,无可竞争,于是乎会博得更多的同情而不是为难,这样的日子当然好过,这可能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境界。
无论是以小组为圈子,还是以宿舍为单元;无论是主流党干,还是边缘文青,77摄影班的每一位同学和着一个时代与一所大学的律动,演奏出各自人生的哆咪嗦。那些纯真和复杂,朦胧与真实,独属于他们,独属于一个美好的胶片时代。
人生漫长,只此一段。
05.我为什么要赞美你
用影像记录和发现社会;
用行动参与和呼应时代;
用文字迎接和拥抱春天;
在路上,77摄影班曾经和一个于反思中求变的大国一同辗转……
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1978年之于中国,就好像1977年高考之于77摄影班,堪称一个大转折的时刻。这一年的中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在做着同一个事情,自上而下叫做拨乱反正,自下而上叫做民主觉醒。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一个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一个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标准提出来的。“唯一标准”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两者尖锐对立,一时间,理论界和政界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文革”虽然结束,但如何评价“文革”?上层的争鸣如黄钟大吕,坊间的动静也从未消停。若把76年天安门事件看做民众意志的初体现,那么稍后的星星画派、朦胧诗、伤痕文学浮出水面,恰恰是民间各方力量自下而上的觉醒与反思。77摄影班同样被卷入到这股汹涌的思潮中。
任金州:我们这一代人生于毛泽东时代,是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中成长的,同时又切身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重创。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面对各种思潮,我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与辨别。
比任金州年龄稍小的另外一位老大哥钟大年,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他的反馈有着一贯的持重。
钟大年:我还穿着老棉裤老棉袄时,交际舞、喇叭裤已经被风行、被礼赞;我还贪婪于巴尔扎克、爱森斯坦、斯坦尼体系这些艺术传统时,星星画派、伤痕文学、朦胧诗等等已经强烈地冲击着那时的文艺青年;当我在为终于脱离了政治有一个专业可学而庆幸时,民主墙、三角地、竞选学生会主席一类的政治游戏成为大学校园的一道风景线……农民毕竟是农民,面对一个全新的校园生活和变化的时代,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
但是,并非所有的老大哥们都在思考,都在观望。和钟大年同岁的叶青醇同学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率性与高调。
正如人本心理学家罗杰斯在《个人形成论》的开篇从自身家庭背景谈起,这绝对是观察了解一个人的方法论。出生于世代华侨家庭,父辈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首个航空大队,自小在三里河总参大院长大,入伍期间最好的伙伴不是战友,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英文。以上信息虽然只是叶同学家庭和个人背景的只言片语,但足可以让我们看到大院子弟——叶青醇的些许底色:骄傲、激进、文艺、感性、敏锐,还有一点,用当下的话说,就是“潮爆”。
70年代末,国人渐渐有了文艺生活,交谊舞和国标舞开始风行。周末把书架子一收,广院的老图书馆于是就成了临时舞厅,在一众潮男潮女当中,叶同学凭借潇洒的外表和出挑的舞姿,很快成为全校大名鼎鼎的舞会王子,吸引了很多漂亮女生的青睐与追捧。由于父母在香港工作,叶同学真是大有潮的资本,不仅第一个将双卡录音机拎进了广院,也是广院第一个拥有日本进口摩托车的学生。
叶同学的潮不仅体现在外在,他的潮更在骨子里。天安门“四五运动”爆发时,还是工人的他不仅给予积极关注,而且还动手写了多首激情昂扬的诗歌。当北岛在诗作《回答》中以一句石破天惊的“我──不──相──信!”震醒茫茫黑夜时,叶青醇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思考进入了更深层和更强烈的悸动。
随着国人对于“文革”反思和争鸣的不断深入,1978年11月出现的西单民主墙,彰显出人民要求民主的迫切愿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叶青醇发起组织了一场“民主讨论会”,在校园搅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
叶青醇:我作为摄影班的代表和播音班的白羽、编采班的郑固固共同策划和组织了这次讨论会。我们顶着被开除党籍的压力,承受着一些同学的冷嘲热讽,也面对着广大师生的热情期待。
11月28号上午,叶青醇与77播音班的白羽、77编采班的郑固固商量之后,在学院贴出了“新闻系民主座谈会”的海报。时间是晚饭后,地点在一号教学楼二层大教室。但是没有落实重点发言的人,因为敏感,所以名单无法确定。
晚饭前,支部书记岑传理找到叶青醇谈了话,暗示系里不同意这个座谈会。叶同学听完心都凉了,但是通知已发,只好硬着头皮开了。
叶青醇:晚上6点半时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虽然很多人是来观望的,但也是一种支持,心里多少有些安慰。我先做了一个说明:这次座谈会是响应《中国青年报》关于开展“民主与法制”讨论的号召,在同学中对关乎国家命运的民主与法制问题进行讨论。
叶青醇讲完之后,有片刻的冷场,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着、期待着……谁是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人?此刻,多么需要一个富有勇气的同学打破这个局面。于是,叶同学又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这时忽然有人大声说:小宋要讲!76级艺术系的小宋心一横走到前面的麦克风前。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应该对毛主席有个正确的评价,如果不破除对个人的迷信,在中国就不可能建立起法制和民主。他很好地开了头一炮。
接着是白羽发言,他重点讲了“民主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他以南斯拉夫为例子,因为政治上的民主,该国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快的,基本达到了欧洲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随后是外语系的一个毕业生,他讲得趣味横生,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特别是他在模仿反对学生讨论民主的一个校领导时,更引起一阵爆笑。严肃的话题变得轻松了。
班长任金州以参加座谈会的实际行动支持了叶青醇的这一激进之举。
任金州:叶青醇他们的讲话我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但是叶青醇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没有现代化的思想,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社会。’其意是首先要解决思想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的思想很受禁锢,有什么思想?党中央、毛主席、国家早把思想路线弄完了,你的任务就是学习和执行,不能对现行体制进行思考,而叶的意思是对现行体制思考,这个体制不是现代化的,此类的碰撞思想对我们启发都很大。虽然我也是学生,但我是班长,稍稍有点责任感,我不希望这个班的同学们出现一些事情。“文革”中对我毕竟有些修炼,希望在稳妥中发展,所以我在发言中强调对毛泽东要一分为二,对现行体制也要一分为二。
在任金州、马国力发言之后,播音班的老大哥汪良终于克服了犹豫,发表了一通不断引起掌声的演讲。气氛越来越活跃,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最后一个是程鹤麟,他谈的是我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其言辞之激烈令人瞠目结舌。
广院的民主座谈会在一阵喧嚣的激昂中结束,没有结束的是师生们对于中国“文革”和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再思考。77摄影班的这一动作,在广院上下引发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有“开除叶青醇党籍”的声音,但这样的声音已经成不了主流,77级再一次以自己的特立独行表现了一代大学生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独立思考。
若干年后,叶青醇同学撰文,回忆“广院民主座谈会”,30年风雨磨炼,率性和赤诚依旧未改:
一年后,“西单民主墙”被推到了,但在人民心中却竖立起了一座民主墙。
记得当时流传着一首西单民主墙上的诗:“我的朋友,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再见!我能对你说些什么?说春天的严寒?说枯萎的腊梅?不!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我们应该带着尊严告别,不是吗?”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