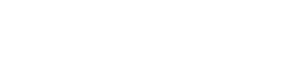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新闻学学科带头人之一、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自1959年大学毕业以风华正茂之年跨入当时刚刚成为本科院校的北京广播学院,至今已满头银发。40年来,赵玉明教授呕心沥血于中国广播电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成为这一新闻学新兴分支学科创始人和建设者之一。
1992年,为表彰他在高等教育事业上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决定发给他政府特殊津贴。在他的身上汇聚了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新闻学学科规划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等一系列分明与实力和学养相关的社会职衔,更重要的则是他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实绩。在北京广播学院成立45周年前夕,我们访问了他。
笔者:今年广院迎来了建校45周年,您也伴随着它度过了40个春秋。在大家的心目中,您这40年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硕果累累。您是怎样走过这40年的呢?
赵教授: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广播电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光阴荏苒,已经40个年头了。虽然40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大半生的时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所经历的这40年,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分作前后两个阶段。
三中全会前的20年中,知识分子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胆战心惊地度过的。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勉强维持,谈不上科学研究。倒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政治运动少了些,学院又一度暂停招生,我才有时间冒着走“白专道路”的风险,跑到北京图书馆和广播事业局档案室,泡在资料堆里查阅、抄录旧中国和解放区的广播历史材料,仅解放战争时期的广播原稿摞起来就有一米多高。那时没有复印机,凡是对研究广播史有价值的史料,我都是一页页地抄写下来的。但也正是这些原始资料的积累,使我对旧中国特别是解放区广播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不停顿地大批判、斗批改、下农村、去干校……直至广播学院停办,又使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1973年,广播学院恢复,我才又重新走上教学岗位。当时的新闻系几十名教师中仅有两名“文革”前的讲师,其余都是四十岁左右的“老助教”,每月工资五六十元,大家彼此彼此,仍然不停地在“运动”中苦熬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广播学院获得了新生。广大教师多年来被压抑的教学科研的积极性随着思想的解放空前地迸发出来。在院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有众多像温济泽、周新武、杨兆麟、齐越等“老广播”热心的指导、帮助,我过去关于广播历史调查研究工作的设想一个个地成为现实:组织并参加了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旧址考察,广泛地征集了解放区广播回忆录、查阅了民国时期的广播历史档案、编印了多种广播历史书刊、出版了《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特别使我兴奋和激动的是,我们通过实地考察、访问“老广播”并核查当年的报刊档案后,提出的更改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的建议,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使中国人民广播的创建纪念日从1945年9月5日追溯到1940年12月30日。这不仅丰富和充实了解放区广播史的内容,而且为弘扬延安广播的光荣传统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广播学院的招生、教学、科研、职称评聘等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轨。首先是一批“老助教”定职为讲师,又过了几年,新闻系也陆续有了副教授、教授。1988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已经52岁了,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和现在三十多岁的优秀青年教师即可晋升教授,简直不可同日而语。1979年,我和王珏老师在广播学院首次招收研究生。1981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二十多年来追求的目标。1983年起我走上新闻系领导岗位,1989年3月开始担任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直到去年2月,从学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花甲之年又回到新闻系,专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回首这二十年,从我个人的经历中,切身体会到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再也不是一句空话。在十多年行政、教学“双肩挑”的岗位上,我感到有做不完的工作,总想着尽可能地多干点、干好点,不辜负党和学校对我的期望。回首往事,对比前后两个二十年,使我感慨万千,应当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晚年壮志,奋斗不已,迎接21世纪的到来。
笔者:对于您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方汉奇教授曾在序中评价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记述1923-1949年间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专著”,“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中国新闻史的内容”。您能不能谈一下撰写这本书的缘由和经过?
赵教授:撰写《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主要是从教学需要考虑的。我国的广播事业从1923年上海出现第一座电台开始算起,至今也只不过七十多年的历史。在长达一千二百多年以报刊为主的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中,广播的历史只是很短的一段。研究它的人很少。我从1959年开始从事中国广播史教学工作起,就曾暗下决心,一定要编写出一本中国广播史来,没有想到的是,我为这个目标竟然曲折奋斗了二十多年,才成为现实。80年代初,我开始着手三件事,第一是多方收集、分类整理了已有的广播史料,特别是开始征集解放区广播回忆录;第二,陆续主持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两集)、《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和《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等书;第三,开始构思中国现代广播史的框架,并陆续写成初稿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连载,后来还印成小册子,名曰《中国广播简史》,并被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编印的《全国新闻系统测试复习提纲》指定为参考书目之一。1986年经修改充实后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为名印成内部教材使用。第二年才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至今包括再版重印,印数已达两万册以上。这本书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1990年主办的首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中曾荣获二等奖。
方汉奇教授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正是受他讲授中国报刊史的启迪,我才倾心于中国广播史的。他把《简史》称作“专著”,实在是过誉之言。论字数,《简史》不过十多万字,只不过因为它是第一部,是填补专业史的空白之作,所以才引起新闻史学界和广播电视系统的重视和好评。
《简史》毕竟是简史,还不足以反映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广播史的全貌,尤其是没有涉及新中国的广播电视的发展。现在我已从学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今后将全力以赴,争取尽快把主持编撰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修改定稿。笔者:除了《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您还主持编纂过《广播电视简明辞典》、《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等一批专业工具书。这些工具书现在已成为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和研究者了解广播电视不可或缺的案头读物。请您谈一谈这几本书对广播电视工作者和研究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赵教授:编纂《广播电视简明辞典》是1987年提出的,当时我在新闻系担任代系主任职务,主要分管教学科研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广播电视学是我国年轻的、具有蓬勃发展前景的学科,但是直到80年代中期还没有一本广播电视专业的工具书,给广播电视的研究人员特别是众多师生的工作和学习带来诸多不便。编纂辞典的建议,得到当时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由新闻系牵头,组织校内部分教师还邀请了中央三台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分头撰写了1800多个条目。1989年在校庆前夕,我国第一部中型广播电视专业辞典终于问世了。顺便说一句,这本辞典早已售缺,现在正组织力量加以充实、修订,大概今年新版的《广播电视辞典》将会与读者见面。
引发我倡议编纂《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的缘由是,80年代初期,我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卷》的部分组织、撰稿工作。按照百科全书的编写体例,新闻卷中只收入涉及新闻方面的广播电视条目,而广播电视技术的条目,则列入电子学卷的范围,至于广播剧、电视剧之类的广播电视文艺条目,又要到文学卷中去查找。这样一来,完整的广播电视知识却被分割成了三块,这对需要寻求广播电视完整知识的读者来说,太不方便了。有鉴于此,在90年代初,我积极倡议并组织学院的部分教师开始编写这部工具书。在框架体例、部类划分、条目设置、目录编排、释文撰写和资料选编等方面几经斟酌,才比较好地体现出广播电视学科已有的基本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于1994年出版,恰好成为校庆40周年的献礼。后来,这部《百科全书》获得了广电部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是受原广电部、现国家广电总局的委托,由广院负责编纂的。由一个学校担负一个行业的年鉴的编纂工作,这在数以千计的高校中是不多见的,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广院在广电系统乃至全国高校中的学术地位。从1986年创刊到现在,《年鉴》已出版了12卷,总字数累计达两千万字左右,我先后担任编委、副主编、主编工作,亲眼看着它成长为今天这个规模,内心倍感欣慰。每一版年鉴都是对上一年度全国广播电视发展的情况、新的进展与经验的汇总,为推动我国广播电视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全面的材料,同时为广播电视的教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对广播电视史的教研工作来说更是受益匪浅。通过参加编纂这几种专业工具书,扩展了我的研究视野,获得了多方面的广播电视专业知识,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科研组织工作能力。
笔者:据我们了解,您不但在学术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在教学方面也有不少独到之处,很受学生尊敬。自从1979年您在广院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您指导学生撰写的毕业论文大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有的还填补了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的空白。那么,您是怎样指导学生的呢?
赵教授:教师的责任在于教书育人。在教学方面,我比较注重教给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么。现在我国的高校教育还是注重知识的传授,对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有的老师虽然认识到了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可在实际教学中还是摆脱不了“灌输式”、“填鸭式”的影响,教学效果不很理想。我为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新闻史》课,经常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提前布置好讨论题目,引导学生查阅各种书刊资料对讨论的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思考,准备讨论提纲,在课堂上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对我也很有启发。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能力,我布置专题作业时,往往只划定范围,不限定题目,目的在于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积极性。这对于研究生教育尤为重要,因为他们以后都要独立地完成毕业论文。
在育人方面,我觉得对待学生既要爱护,又要严格,而爱护更多地体现在严格上。比如在课堂上我要求他们不迟到,关闭BP机,发言提纲和作业要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不能敷衍塞责等,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有益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识修养,不容忽视。对一般研究生严,对中国广播电视史方向的研究生,我的要求就更严。曾经有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我就决定推迟半年进行答辩。不能因为他是我指导的学生而有任何偏袒,相反,对我直接指导的学生要求应当更严一些。历史是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因此,从事历史的研究不能有丝毫马虎,来不得半点浮躁,我常引用史学前辈的一句话来鞭策自己,同时也用来教育我的学生: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
研究生学习三年的成果很大程度体现在他们的毕业论文上,因此在确定毕业论文选题之前,我经常把平时思考的一些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提出来供他们参考。广播电视史方面的论文选题既要有历史价值,也不能脱离现代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需要。我指导过的毕业论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广播历史方面的,如79级研究生郭镇之的《论旧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历史命运》、84级哈艳秋的《伪满广播简论》、94级范晓晶的《民国时期广播报刊研究》等;一类是涉及当代广播电视改革和发展的,如85级孙鸥的《中国国际广播宣传改革探析》、87级李琦的《广播电视法刍议》和喻山澜的《新时期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探析》、88级袁军的《论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广播电视广告》、91级徐晖明的《广播电视志刍议》等,从论文内容上来说还是很广泛的。另外,选题要适当,不能过窄,过窄就可能缺乏实质内容,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但也不能过宽,过宽则未必是一个硕士研究生所能驾驭的。资料也是这样,太少缺乏研究基础,很难得出正确、科学的结论;太多又没足够的时间、精力。因此,作为指导老师,不仅要在选题的方向上把关,还要为学生准备适当的资料。比如,为了指导学生撰写广播电视志方面的论文,我就购买了《中国地方志辞典》,补订了全套的《中国地方志》杂志,还收集了省、地、县三级的广播电视志书200多种。这些单靠学生完成有很大困难,作为教师平时要注意积累和搜集。我把历年来收集、购买到的有关新闻史,特别是广播电视史的书刊资料搞了个“史志资料中心”,基本上可以满足研究生查阅资料的需要。再就是要考虑学生的特长、爱好,像哈艳秋撰写的关于伪满广播的论文,就充分利用了她的日语专长,也填补了我国伪满广播研究的空白。这一课题的成果,还引起了日本有关大学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