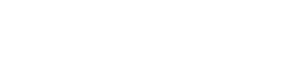作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一生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可他偏偏与“九”字有缘:1959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是第一批本科生的教师;1979年,他成为广播学院第一批硕士生导师之一;1989年,他担任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任期九年;1999年,他又成为广播学院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2004年4月,他被推选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一届任期是五年。今天,赵玉明老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如果我能健康地工作到2009年,到那时,我可以欣慰地说,我把毕生精力都献给新闻教育事业了。”
披苦沥难出名校 倾情广院育英才
记者:从您的履历中了解到,您的初中、高中学习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对您最有影响的人是谁?给您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赵玉明:我出生在山西农村,幼年随经商的父亲迁到天津。中小学都是在天津上的,新中国成立那年正好开始上初中。后来,因为我父亲病了,全家就从天津搬回了老家,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天津上学,一直到高中毕业。
1954年,高二的暑假,我回了一趟家,当时父亲已重病在身。但没等到我寒假回去,这年冬天,我从母亲的来信中知道了父亲去世的噩耗。母亲说父亲已经入土为安了,让我留在天津安心学习。1955年1月,寒假到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家乡。因为这年的夏天就高中毕业了,所以,我就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上学,还是参加工作,挣些钱补助家用。当时我们家的
![]()
① 原载王永亮等编著《传媒精神———高层权威解读传媒》,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访问者当时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博士生。
情况是这样:我父亲不到50岁就去世了,母亲不到40岁,家里孤灯一盏,一个大炕,上面躺着四个睡熟的弟弟———最大的10岁,还有7岁的、4岁的,最小的刚三个多月。我就跟母亲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再上学家里就没法过了。当时,母亲说了一句话:“要能考上,你就接着上,家里怎么也过得去。”我今天回想,这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最关键的决定,恐怕就是这次。母亲当时要是让我自己选择的话,那可能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想,每个人家庭情况可能都不完全一样,但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子女的一生,确实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母亲这句话的激励之下,我坚定了自己的决心:继续念下去,争取考大学。
我母亲于1996年2月去世,时年虚岁80。我对不起她的是,因公务繁忙,未能在她临终前见上一面。在返乡奔丧的火车上,念及母亲的养育之恩,彻夜难眠,天亮前头脑中形成一副挽联:“含辛茹苦六十载,养育五子成人;任劳任怨万千日,培植四世同堂。”悼念之日,我含泪把这副挽联献于母亲的灵前。
记者:对您来说,苦难是最好的大学,而您母亲真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您报考大学面临着哪些选择?
赵玉明:我在天津三中读的高中,这是天津的一所名校,现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我从私立的初中考上公立的高中不是很容易的。高中毕业时报考大学不像现在按专业报名,哪个专业好,就考哪个,当时是按系报名。我们学校的风气是奔名校。我的文科、理科都凑合,但因为受语文老师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就决定考中文系。最有名的中文系当数北京大学,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北大填到了第一志愿里。很幸运,1955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当年北大中文系大概招了200多人,天津只考上了几个人。入学以后,我了解到中文系有两个专业:中文专业和新闻专业。填表的时候,我填了中文,想都没想过要搞新闻,后来却被分配到了新闻专业。其实,谈到中文,我还知道一些东西;可说到新闻,我连它是什么也不知道。但当时的青年人都有一个信念:作为共青团员,党分配到哪里就去哪里。所以,我就学起了新闻。从1955年跟新闻结缘,走进这个圈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年了。
记者: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后来合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您是亲身经历者,您能讲述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吗?
赵玉明:当时北大55级的新闻专业有三个班100人左右。1958年6月,
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合并,罗列老师带着北大新闻专业全体师生,从燕园到了城里的铁狮子胡同一号,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这里曾是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地。当年人民大学有几个系在这里,但学校的本部还是在西郊。甘惜分、方汉奇、张隆栋、郑兴东和何梓华等老师也都一起到了人大。人民大学新闻系是1955年办的,明年恰好是50周年,我们虽然是1958年合并进去的,但仍算是55级的,所以我们在1959年毕业的时候,居然成了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一届毕业生。1998年,我们这批同学也收到来自北大校友会的邀请参加百年校庆活动,成为“北大加人大”校友。能够得到两所著名学府的共同承认,我们深感荣幸和自豪。
记者:我看过您的简历,在北大、人大的学习时间是从1955年到1959年,当时正赶上1957年的“反右”,您受到影响了吗?
赵玉明:遗憾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正常的学习受到冲击。我本人是个读书人,每天过着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对政治运动不是很感兴趣。作为一个团员,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当时来说就算一个问题了,加上又说了一些当时不该说的话,当时认为我思想有右倾情绪,于是给了我一个团内警告处分。当然,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来信为我平反了。 |
我觉得在北大的这两年,认真学习了新闻理论、新闻史、编辑采访课,为我打下了基础。在这里,我初步了解了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和实践。从
1955年秋到1958年春,在北大的这段时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
“北大八百日,读书好时光。”
记者:您到了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那里您经历了什么样的教育?
赵玉明:1958年春天,北大的新闻专业并入到人民大学。如果说我在北大主要是打新闻基础的话,那么在人民大学则主要就是新闻实践了。我们是
6月份过去的,七八月就到了河北日报社实习。河北日报社实习完了以后,
10月份又到山西日报社实习。山西日报社实习完以后,就到1959年的春天了,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在人大的这一段正好赶上“大跃进”,学校的正常教学受到了影响,我实习的两个报社也受到“大跃进”的影响。记得当时采访大炼钢铁写的消息标题是《守炉餐,伴炉眠,十八次失败心不甘》。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时有一个矿山组织工人写诗,写了一万首诗,编辑部来电话叫我连夜坐吉普车到矿山去选诗,结果一篇也没选上。当时在那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我也跟着吹了不少牛,今天想来仍然脸红心跳。在这两个报社的实习,一方面,让我真切地感受了“大跃进”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实习生,这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在人民大学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安岗老师,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同时兼任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他上课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晨《人民日报》刊登些什么,上课时他就讲什么。包括头天晚上《人民日报》处理了什么稿子,中央有什么指示,第二天在课堂上他都给大家讲。等我们下了课一看报,确实就是像老师讲的那样。安岗上课的时候讲过,作为一个记者要“多谋善断”,过了许多年,再看有关《人民日报》的回忆录,才知道这是当年毛主席讲的。人民大学新闻系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之紧密,别的学校确实无法与之相比。
总之,如果说今天我对党的新闻工作、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这些基本的东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想就是在北大和人大打下的基础。
记者:您从1959年大学毕业到广播学院执教,至今已有45年了,有没有什么事情令您特别难忘?
赵玉明:说到第一个难忘,我想广播学院初建那几年的日子是非常值得我回忆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赶上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广播学院本身条件并不算好:就师资来讲,不论是广播局来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应届生,都没有授课经验,并不是很强;就设备条件看,也是非常简陋的,跟现在没法比。尽管条件不好,但是也有不少有利因素。一方面由于院系领导对办学确实是非常重视,他们的努力为广播学院的成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当年为了办广播学院,中央广播局副局长周新武同志兼任院长,副院长左荧同志兼任新闻系的主任。这些同志都是老革命、老党员,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创业者。在院系领导的带领下,一批中青年老师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另一方面,59、60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出身贫寒,考上大学是相当不易的,所以,这些学生学习非常刻苦,他们扎扎实实地学习,收获了知识,绝大多数人后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为广播学院增了光添了彩。虽然这批学生学习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条件很不好,但正像后来国际台台长张振华作为校友所写的文章中提到的:“贫困也是财富。”中国有句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条件好了,如果不正确对待,反而误了学生成才;条件不好,反而激励学生成才。当年毕业之后,并没有现在的“韬奋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等这些奖项,但他们确实非常踏实,干得非常出色。给59、60这两级学生上完广播史的课以后,1961-1963年学院基本上没有招生,但我并没有闲下来。于是,我就代起了采访课,而且要带实习。那时候学生实习是非常严格的,需要老师跟随指导。我曾经带着学生去湖北武汉台实习,一待就是半年,现在到了武汉,有些人还是一见如故。因为上学时我只在报社实习过,并没干过广播工作,所以当时我是和学生一起采访、写稿的,对我来讲,这也是一种实习和锻炼。
64、65级的学生又赶上“文革”了,他们的经历大都非常坎坷。今年50周年校庆,65级2班校友最近有一次聚会,40多人回来了30多人,大家坐下来谈自己毕业后的经历,真是非常令人感慨。59、60级的毕业生分配基本上是省级以上广播电台,而64、65级的学生分配基本上没有在省里的,大都在县里甚至乡里。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第二个难忘是广播学院近十年来实现了几个大的跨越,尤其是跨世纪的几年间广播学院的大发展。由普通高校变成国家“211工程”的重点院校;由比较单一的广电专业高校变成全媒体的高校;由最初的千人院校发展成万人大学;由广电部主管的行业高校变成由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由本科院校变成具有完整体系,包括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等办学层次的大学;由教学型院校向教学研究型院校过渡。 |
第三个难忘是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没离开广电史,没离开学生。从1959年起我教了30年本科生,从1979年起教了20年硕士生,从1999年起指导博士生,如果能教上10年博士生就好了,到现在已经6年了。我到外地出差的时候,除了正常的工作任务以外,还特别去看望一下各地的学生。迄今为止,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我都去过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到县市,从海南到黑龙江,从上海到西藏,全国各地都有广院的学生,真是桃李遍及广电园地。
转型之际显从容 立德敬业勇创新
记者:从1984年到1989年,您从一个单纯的业务型的教学的老师,到了新闻系领导的岗位上,这五年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做了哪些改革创新?
赵玉明:从1984年起我开始担任新闻系的副主任,分管教学研究,后来又担任主任,直至1989年3月担任院领导。从一个单纯的业务型的教学的老师,到了新闻系的系主任的岗位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转变。我在新闻系领导岗位上的五年,为自己在教学、科研、管理上都奠定了基础。因为我原来是搞广播史的,虽然是教研室主任,但教研室也就两三个人,任务不重。作为系里的领导来讲,要管起全系的教学科研工作,就要不断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新闻系为广播学院开办之初的三大系之一。1980年学院调整文科教学机构,以新闻系原有各专业为基础重新组建为四个教学系(新闻系、播音系、文编系和电视系)、一个新闻研究所和一个语言文学部。新组建的新闻系是在原广播业务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的,当时全系只有教职员工20人左右,专业也只有一个编采专业,就是现在的新闻学专业,而且办学层次比较单一,就是本科。1979年曾经招过硕士研究生,后来中断了。作为一个小新闻系,当时我们跟人大、复旦新闻系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在我接任系领导以后的五年,我和新闻系的其他领导与全系教职员工一起,在前人的基础上,逐步地把新闻系发展起来了。我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开创:
第一,筹建了广告专业,把单纯的新闻专业变成了两个专业。广告专业于1988年开办,1989年开始招生。当时大陆广告专业只有一家,就是厦门大学,我们是第二家。那时候办一个专业,报告要打到教育部去,不像现在,学校说办就可以办了。
第二,办学层次有了显著增长。1980年刚分系的时候,新闻系只有一个办学层次———本科,经过几年努力之后,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都发展起来了。在83级以中央电台为主的编采干专班之后,又招收了84级以地方台为主的编采干专班,还招收了84级大专班(北京班),85级大专班(山东班)。1985年、1987年先后招收两届研究生班,主要为中央电台、国际台培训干部。1987年又为本院和兄弟院校开办了助教进修班。同时本校的新闻学专业的函授班也办了起来,还为中央电大开设了广播专题讲座课,办学层次有了显著提高。
第三,编写了我们新闻系的第一代教材。在这之前,新闻系没有系列教材,只有教学提纲、参考书。现在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材已经有了第三代、第四代教材,那么,1986年我们编的是第一代教材,共8本,从理论、历史到业务,使新闻系的教学逐步发展了起来,因为办学第一就是教师,第二就是教材,没有这两样是办不好学的。第四,扩大了新闻系的影响。一是扩大新闻系在学校的影响,二是扩大新闻系在广电系统的影响。我们办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编辞典,首先倡议编纂中国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即后来的《广播电视简明辞典》,是由新闻系首先提议,然后和兄弟系合作的;再一个就是召开了广播学院第一次研讨会。现在研讨会多得很,但过去就很少了。我们召开了大概是广播学院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研讨会,就是1986年召开的“解放区广播史座谈会”,那时还不叫研讨会,但实质上是研讨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员层次之高,过去也是少有的,就是原来解放区的老广播凡是现在北京的几乎全请来了。参加人员包括中央广播局的第一任局长李强,他当时是国务院顾问,现在用级别来讲是副总理级。还有原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部主任温济泽,我们学校第一任老院长、原华东台台长周新武以及解放区广播电台的许多老同志。我们把这些老广播、老编辑、老播音员、老技术工作者请来,开了一次“解放区广播史座谈会”,后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策划成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使得新闻系的影响逐步向外扩展。当时我还担任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副秘书长,参与筹备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因为广播电视学会成立的时候,中央三台各出一位副秘书长,广播学院也出一位副秘书长,我是从新闻系代表广播学院参加的。后来我当了副院长还是副秘书长,他们说要不要换人,我说换也要换广播学院的,不能说把我换了,就把广播学院的影响消除了。要把一个系发展起来,除了内部办学和搞科研,还要把它的影响逐步扩大。经过努力,新闻系先后被评为学院的先进集体以及北京市新闻系统的先进集体。这是我们做出的一些成绩。 |
记者:1989年您是如何走上学院领导岗位的?九年中的体会如何?
赵玉明:1989年走上学院领导岗位,原来也是没想到的。1988年冬天学院领导班子酝酿换届,当时全院的系处级干部,以及工会的代表,大概有一二百人一起开会推荐院领导人选。从不提名投票的结果中选出前三名,我是其中之一。经过民主评议、学院党委考核并经广电部批准,我于1989年3月起担任副院长。那时我53岁,在当时来讲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的工作就是分管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后来又加上年鉴和学院董事会的工作。我想作为一个双肩挑的干部,到了学院的领导岗位,跟在系里面临的情况又不太一样。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学院的领导干部,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什么都不放弃。所以我想应当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科研的管理上。如果说当系主任的时候管理和个人教学的比例是五比五的话,当院领导就要三七开,甚至二八开,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教学科研的管理上。因为毕竟是几千人的学院,教学科研让你管,在个人的教学科研上就要有所放弃。当时我是这样做的:第一就是教学不断线。本科生我就不教了,因为顾不过来了,所以我只教研究生。研究生就教一门课,新闻史。而且我只带一位研究生,一位研究生毕业了我再带第二位。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属于著作、论文的评奖我还参加,因为我觉得著作、论文的评奖有助于教学科研的管理。但是广电节目、新闻作品等方面的评奖我就不参加了,同时谢绝一切校内外的短训班讲课任务。我觉得作为一个院领导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管理上。
在学校领导岗位上的九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忙于日常的教学科研、行政事务工作,其间酸甜苦辣的体会,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但我常想前人有句话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庆祝建校50年征文之际,我写了《几件实事的回忆》一文,回顾了在两届领导班子的几年间,在“班长”的主持和支持下,确实做成了几件对于学校建设长期有益的实事,如倡议建立和组织实施了“中央三台奖学(教)金”;促使《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工作走上正常运转的轨道;组建了首届学院董事会,筹措了近千万元基金,投入了“211工程”建设;推动设立了广电部的部级科研立项和部级科研奖,以及初步改变了学校图书馆图书经费紧缺的局面等,总算没有辜负广大师生对自己的信任和期盼。文中我还特意写了两件引以为憾、没有办成的“实事”,热切希望后来的有志之士积极促成,了却我的未遂心愿。其中一件是功败垂成的旨在奖励广电系统优秀播音员、主持人和播音教师的部级“齐越奖”;另一件是在中国记协主持的“韬奋新闻奖”评选中建议根据《评选办法》的规定,将优秀的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列入参评范围。为此,作为三届“韬奋新闻奖”的评委,我曾多次在评选会上呼吁,但终因多种原因,未能促成。
记者:从学校领导的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您人生中的又一次转变,请问您是如何面对这次转变的呢?
赵玉明:一般离开领导岗位的年龄是60岁,59岁的时候我就提出“站好最后一班岗”,想早点儿退下来。是想趁着身体好,还可以做些教学科研的工作,行政这些工作最好是让更年轻的同志来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到
1998年2月换届有了适当人选时才退下来。从1989年3月到1998年2月,又是一个九年。这个转变我早有准备,不存在失落感,反而更充实了。因为原来在领导岗位上很多行政工作不得不做,下来以后则更能集中精力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我还没有退休,还在发挥余热。当前我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个是带好博士生,我从1999年开始带博士生;第二个是继续担任《年鉴》主编,因为暂时没有适当人选,我也表示只干一届;第三个就是一些社会学术工作,其中包括广电史研委会会长。我在2004年4月份又担任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长。
此外,做新闻史研究还使我收获了友谊,我与一些老革命、老同志结成了忘年之交,像梅益、吴冷西、温济泽、周新武等同志。我们这些与历史打交道的人,应该把前一辈人的成果记载下来,尽量把它们挖掘出来变为财富,不要让它们埋没掉,因为今天的辉煌都是建立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的。最近几年,我先后写了几篇缅怀他们的文章,还参与了《温济泽纪念文集》、《周新武同志纪念文集》和《梅益同志纪念文集》等书的组稿和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