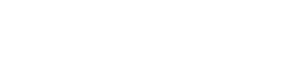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建校55周年。本人195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至今恰好50年。回顾国史、校史和个人的成长史,深深感到个人的成长与国运、校运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国运盛则校运兴,校运兴则个人成长顺利;反之,若国家发展遭遇挫折,则学校必然衰微,个人的前途命运也随之沉浮多舛。国庆长假,浮想联翩,试以1949年起六十甲子的每个“九”字年为序,串联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作为对新中国60年大庆的一份心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首都北京举行。当年我13岁,正在天津读书,刚刚迈进中学门槛。那一天,我和天津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齐聚在大广场,怀着喜悦的心情,从下午3点到傍晚,聆听了从广播中传来的“开国大典”的盛况。随后,我们高唱革命歌曲,举行了欢庆游行,直到午夜始告结束。
欢呼新中国诞生的热情化为建设新中国而奋发学习的动力。新中国最初的10年,也正是我寒窗苦读的10年。高中毕业前,我加入了共青团。随后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来到了首都。1955年的国庆节,我和许多外地同学一起第一次参加了国庆游行,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1958年春天,随着新闻系科的调整,我转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继续学习。
1959年,十年大庆前夕,我结束了在人民大学的学业,来到刚刚升格为本科院校的北京广播学院,成为新闻系的第一批本科教师。新创建的广院位于复兴门外,只有一座5层灰楼,虽有校但无园,教学设备简陋,但受“大跃进”精神的鼓舞,全校千余名师生干劲十足。我们这批刚从不同文科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对广播电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是学习劲头不减当年。在“老广播”的带领下,我们边干边学边教,逐步熟悉教学业务,逐步成长起来。
① 原载《中国传媒大学校报》2009年11月3日(上)、11月19日(下),《中国传媒观察》
2010年第1~2期合刊,《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11年第2期,均刊载。
创建伊始的广播学院恰逢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学校面临下马的厄运。1961年起学校停止招生,新闻系教师由50多人锐减到30余人。在瓜菜代饭的日子里,留下来的教师仍然坚持正常工作,并先后使59级、60级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送他们走上工作岗位。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从1964年起又恢复正常招生,学校重新走上正轨。
在这期间,最难忘的是,1963年我有幸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了当年的国庆观礼。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位置是在天安门东侧第7台,并在观礼台上巧遇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同志。参加观礼印有国徽的红绸条证,我一直珍藏着,1994年校庆40周年时,我将它捐赠给校史馆供展出用。大概是我工作尚属努力,这一年在个别调整工资中由每月56元升为62元。60年代初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老广播”自己不愿评,我们资格尚浅不够评,有几十名教师的新闻系只有两名讲师。
1969年,党和国家陷入“文革”动乱之中,广播学院也深受其害。
1966年春天,“文革”风暴骤起,为减轻广院学生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冲击的压力,广院全体师生奉命全部迁往今天的定福庄校址(此前只有外语系在定福庄)。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三次到广播学院煽风点火,并污蔑广院是“黑基地”。在“砸烂黑基地”声中,院系领导被打成走资派,一批老党员、老干部被诬蔑为叛徒、特务,普通教师也人人胆战心惊,在两派不停的武斗中度日如年。1969年11月,在战备声中全校师生在军宣队、工宣队的带领下,被迫迁到河北保定附近的望都县农村继续进行“斗、批、改”。当时在校师和教65级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炕头开批斗会,直到第二年夏末始返回北京。随后65级学生陆续分配离校,大多数都到农村厂矿、部队基层锻炼。1970年秋,广院教职工400多人除少数留守外,其余陆续下放到中央广播局河南淮阳“五七干校”,名曰“劳动锻炼”。实际上是在所谓“高温高速练红心”中劳动改造。不久,广播学院在“试行停办”声中下马。 |
1970年的国庆节是在“五七干校”收割声中度过的。我们一边听着广播喇叭中传来的北京国庆活动的报道,一边手拿镰刀高喊“语录”口号,收割成熟的庄稼。劳动之余,仍然是不停地开批判会,既批判别人,也自我批判,总之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那时候劳动量大,人人每顿饭都要吃两三个馒头,有时候还要吃忆苦饭。作为个人幸运的是当年11月初,中央广播局因为要筹备延安广播历史展览,紧急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一年以后,展览之事告一段落,我再次打点行李准备返回干校。出乎意料的是,分配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上班。我在中央台当编辑,参与早晨“报摘”、晚上“联播”节目的工作一年半有余。
1972年冬,传来广院恢复、在淮阳的教职工返回北京的消息。1973年春天,我终于重返定福庄回到新闻系。这时的广院满目荒凉,破败不堪,一号楼教室成了车间,全校职工不过二三百人,开大会时人人马扎一坐,领导站着讲话。我们一边劳动修整校园,一边备课,准备迎接新生。1974年、1975年新闻系两届工农兵学员相继报到,学校开始活跃起来。1976年是大悲大喜之年。粉碎“四人帮”后,学校工作再次走上正轨。1978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77级)入学。当年,学校开始评定职称。第一批名单中只有两名教授、四名副教授。我们这一批工作将近20年的教师被确定为讲师。十多年来又一次普调工资,我由每月62元涨到70元。那年我42岁,已早生华发,四口之家居住在筒子楼的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已有12年了。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祖国大地,广播学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个人的成长也迎来了新的机遇。6月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团总支经过复查通知我:撤销1958年10月因所谓“右倾情绪”错误给予我团内警告处分,压在头上二十多年的政治帽子终于摘掉了。9月,因当年政策的宽松,身为讲师可以招收研究生,我成为我校第一批硕士生导师。
1981年6月,建党60周年前夕,多年宿愿实现,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3年,我晋升为副教授,担负起更多的教学科研任务。
新闻系是广播学院开办之初的三大系之一。1980年学校调整文科教学机构,将新闻系一分为六,分别组建了四个教学系(新闻系、播音系、文编系和电视系)及新闻研究所和语言文学部。我留编在了新组建的新闻系。这时的新闻系是在原广播业务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的,只有教职工20人左右,办有一个本科专业(当时叫编采专业,后改为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小新闻系,与当时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相比差距相当大。80年代初期建系之始的领导,有的调离,有的生病。1984年3月我由广播史教研室主任调升为副系主任,不久因系主任长期卧病,我开始主持日常工作,后为代主任、系主任,至1989年春。五年间,我和其他系领导,团结全系教职员工,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步把新闻系再次发展起来。首先是增加了办学层次,从单一的本科专业,陆续开办起专科(有干专班,普通大专班)、研究生班和助教进修班,招收硕士研究生并开办了函授专修科和中央电大的广播专题讲座,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的办学体系,又发动全系教师编写出版了本校第一代有广播电视特色的新闻学系列教材,共8本。此外,还由新闻系牵头,与全校有关系所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广播电视简明辞典》。1988年经教育部批准,新闻系创办了第二个专业———广告学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这是大陆创办的第二个广告学专业。在这期间,新闻系教师人数增加到30多人,在读各类学生几百人,在高校新闻院系中影响逐步扩大。新闻系先后被评为学校先进集体和北京市新闻系统先进集体,我本人也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并于1988年晋升为教授。
1989年3月,我离开了工作近二十年的新闻系,成为新一届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而且是自建校以来领导班子中的第一个教授。这是未曾料到的。此前1988年冬天,学校领导班子酝酿换届,当时的做法是在全校系处级干部和各方面代表中不提名海选校级干部候选人。最后将获票数最多的前三名作为预备人选,我是其中之一。经过民主评议,学校党委讨论并经广电部批准,我出任副院长,当年我53岁,在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 |
我是个双肩挑干部,既要分管学校的教学研究工作,同时自己又是硕士生导师,并有教学科研任务在身。但与在系里面临的情况大不一样。如果说当系主任的时候,教研管理和个人教研活动的时间比是五比五的话,那么当校领导就至少应是七比三甚至是八比二,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教研管理上,几千人的学校,二十多个专业的教学活动管理对我来说应是头等大事。古人云,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当时我的做法是:教学科研不断线,本科生我就不上课了(今天看来不尽妥当),让给年轻教师,研究生每届只带一个,毕业以后再招第二个。只给研究生上一门课。属于论文、著作的评审我参与,但广电节目、新闻作品的评奖,请其他教授参加。另外,谢绝一切校内外的短训班上课。
在学校领导岗位九年里,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忙于日常的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不必细言。此外,在两届领导班子的几年间,在“班长”的大力支持下,经我倡议并努力也促成了几件对学校建设长期有益的实事,如“中央三台奖”的设立和实施,广电部部级科研立项和部级奖的建立,参与筹建首届学校董事会,筹集资金近千万元以及促使《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扭亏为盈,走上正常运转轨道,并初步改变了学校图书馆经费紧缺的局面。此外,还主持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广电专业百科全书———《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在我任职期间,经广电部推荐,我先后从1991年起担任了中国记协两届理事,并同时出任了三届“韬奋新闻奖”和“范长江新闻奖”的评委。1992年起,我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学学科评审、规划组成员,1996年起任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7年起,又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我在参与上述机构活动和其他学术团体活动中,多方介绍我校特别是新闻传播学教研活动的改革创新成果,扩大了我校在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影响,对我校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和进入“211工程”高校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在这期间,我的居住条件也有了初步改善,并在家中安了电话。
校级领导一般是60岁离岗。1995年,我将近六旬就提出“站好最后一班岗”,希望早点退下来,让位给年富力强的同志,自己也趁着身体好,再做几年教学科研的事,如完成业已批准但尚在进行的由我主持的我校第一个国家级社科项目———《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的编写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我的愿望直到1998年2月才得以实现。离职之际,当年农历正月十五(2月11日)有幸出席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元宵节联欢晚会。随后,以普通教师的身份,我重新回到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新闻系,不过这时已扩建为新闻传播学院了。
1999年,适逢学校申博成功,从本年起我又成为学校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并开始招收了新闻学专业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为了集中精力,我又将招收硕士生和为硕士生讲课的任务让给新来我校任教的中青年博士担任。从那时起,至今我已指导博士生12人,其中9人已先后毕业并获博士学位,另从2004年起又招收博士后科研人员3人,其中两人已出站。我离开学校领导岗位后,先后辞去学校董事会的常务副董事长职务和《年鉴》的日常领导工作,但仍兼任《年鉴》的主编职务。2001年,经学校推荐,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首届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中,我被评为“十佳”之一。
离开学校领导岗位后最初几年集中力量与有关参与的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完成并于200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广电通史著作———《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从2001年起我开始担任我校教育部文科基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首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于2005年起主持该中心的重大课题。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项目,致力于推动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工作。在这期间,继80年代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新闻卷的部分组稿撰稿工作后,又参加了该书(第二版)新闻学分支学科部分条目的有关工作。为了缅怀广院老一辈创业领导人,我参与征集、撰稿并主编了《周新武纪念文集》和《风范长存———左荧同志纪念文集》。除此之外,我从1997年起担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会长,负责规划并组织了四届的中国广电史志研讨会,对推动全国广电史志编修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2009年7月我卸职,改任顾问。2002年,我参与筹建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改组,我开始担任常务副会长主持日常工作,学会秘书处移至我校。2004年起我任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新闻传播学方面的一级社团,联系面多,活动范围广、影响大。为了办好它,我提出了“求真务实”的四字方针,几年来在原来的基础上调动全体会员的积极性,组织开展了多项学术性活动,如国际、国内的研讨会和培训班、红色报刊展,编辑出版《新闻春秋》论文集和专刊、专栏,增设了三个二级分会等,使学会成为推动中国新闻史学繁荣发展的平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甚有声望和影响的一个学术团体。2009年6月,我辞去会长职务,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
进入新世纪,广播学院的发展又迈上新的台阶,2001年成为国家“211工程”高校,2004年校庆50周年之际,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学科研工作拓宽了新领域,取得了新成就,正向世界知名的高水平传媒大学迈进。
2007年1月起,年过七旬的我愉快地办理了退休手续,当年学校授予的我第一批“中国传媒大学突出贡献教授”称号。但实际上,我退而未休,仍在继续上述几项科研工作以及相关工作。
2009年10月1日,古稀之年欣逢新中国60华诞。我是生在困难深重的旧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亲身经历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历经曲折、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几十年,终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初步繁荣富强迈进小康社会的新中国的历史过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几个月前刚刚搬进拆迁后重建的新居里,全家从电视屏幕上收看了60年国庆威武壮观的阅兵仪式和丰富多彩的群众游行,在假日里我和老伴到天安门广场浏览了国庆彩车,到北京展览馆参观了新中国60周年辉煌成就展。一家三代人的喜悦兴奋之情,难于言表。我深深体会到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就没有传媒大学的兴盛发展,也不会有个人为祖国贡献聪明才智的机遇。此时此刻,我不由想起,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学校领导提出北大学子毕业后要能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期盼。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向培养我的母校和祖国回答:我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从1959年大学毕业到今天可以说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了50年。回忆半个世纪的生涯,我一生可以说是有三个“没有离开”,一辈子没有离开广播学院(今天的传媒大学),一辈子没有离开新闻传播的教研工作,一辈子没有离开学生。我在本校教了30年本科生,20年硕士生,10年博士生。每逢离京到外地出差时,除了工作任务外,我总不忘看看广院的毕业生,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到县市,从海南到黑龙江,从上海到西藏,我校的学生可以遍及祖国大地的广电园地内外。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毕竟是已逾古稀之年,虽然身体尚可,但尚未达到北京市人口的平均寿龄79岁。我将用六个字来安排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不闲着,别累着”,度过健康愉快的晚年,迎接新中国70、80华诞。